葛拉斯的詩畫。

「只有目前,當我垂垂老矣,我才找到恰當的形式,在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下談論這件事。」~ 鈞特.葛拉斯。
L:
台北市立美術館,最近有鈞特.葛拉斯(Gunter Grass)的畫作。
因此,就極想飛到台北去。起程之前,看到一家新成立的出版社「原點」把詩和畫出版,命名為《給不讀詩的人》。是的,他發表詩集,比起發表名著「但澤三部曲」還要早。
本年慶祝八十歲大壽的諾貝爾文學獎主,繪畫原來也接近六十年。葛拉斯的畫,以天然景色及動植物為主體,在此之上,或隱約或鮮明的提了詩。他的作品大致上不抽象,景和物實實在在,寓意和表達方向明顯。配了詩的畫,猶如以亮彩斑爛的顏色在畫紙上抺出另一筆雅致與美感。
這位反納粹的「德國良心」,去年出版了很暢銷的自傳《剝洋蔥》,引起坊間一番炒作,針對作者在書內承認自己年少時曾被徵召加入納粹的武裝親衛隊。喧嘩延續至上月,外電報道葛拉斯控告某大跨國書商,否定它旗下公司出版的傳記中所指,他是「自願」加入武裝親衛隊的。據德國媒體所述,該傳記的第一版本,並沒有這筆資料,直至《剝洋蔥》問世,才增訂內容。
「當我十七歲時/手裡拿著我的炊具/一如那個和我孫女露易莎/參加了童軍旅行的人一樣/站在往施普倫貝格的馬路邊/舀著吃起了豌豆仁/一顆榴彈轟了過來/湯汁潑了出來/但我只是輕微地擦傷/並為此感到慶幸」。閱讀至此,L,實在無法不讓人想起,葛拉斯參加納粹的那年,正是十七歲。相對於小說創作,葛拉斯的詩畫視覺藝術,幽幽地多了一份、彷彿經過百年沉澱的蒼桑與寧靜。
(2007.12.14。明報。前書口。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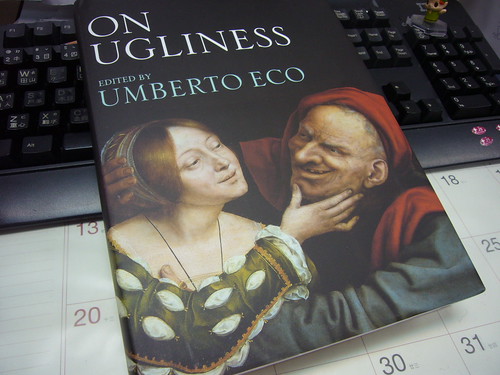
 馬家輝。稿紙以外。
馬家輝。稿紙以外。 劉美兒。晃蕩有時。
劉美兒。晃蕩有時。